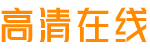文化傳承,真就非得搞得跟博物館文物修復似的,屏息凝神,小心翼翼,生怕一碰就碎?最近網上那個兩歲娃朗朗揮毫潑墨寫對聯的視頻,簡直像一記響亮的耳光,抽在那些把文化傳承捧上天、搞得無比神圣的人臉上。別誤會,我可不是要否定文化傳承的重要性,恰恰相反,我是在質疑我們當下搞傳承的方式是不是跑偏了十萬八千里。

朗朗,一個剛滿兩歲十一個月的小不點,他拿毛筆的動作,與其說是寫字,不如說是拿著個特大號的蠟筆在玩涂鴉。紅紙上歪歪扭扭的幾道墨痕,哪里像什么書法藝術,分明就是小孩子過家家。可就這么個“作品”,他居然能美滋滋地鋪在地上欣賞半天。這場景,說實話,挺讓人忍俊不禁的。我們這些成年人,動輒就談什么“文化根脈”、“精神家園”,仿佛不給孩子報個國學班、書法班,就對不起列祖列宗似的。我們總喜歡給孩子灌輸“這是國粹,你要珍惜”、“這可是老祖宗傳下來的寶貝”之類的大道理,恨不得三歲就給孩子套上“文化小使者”的光環。結果呢?孩子們往往還沒等弄明白這玩意兒是干嘛的,就被嚇得望而卻步了。

朗朗家顯然不是這么干的。桌子上的墨汁、毛筆、硯臺,墻上的書法作品,這環境布置得明明白白——這就是我們家日常的一部分,就跟吃飯喝水一樣自然。朗朗玩毛筆,不是因為他上了什么大師班,而是因為他家里本來就充滿了這些“筆墨紙硯”的氣息。他拿起毛筆,就像我們拿起手機一樣,是再正常不過的行為。這種“玩筆墨”的過程,恰恰是文化啟蒙最好的方式。想想看,兩歲的孩子,能理解什么“永字八法”?能掌握什么“中鋒側鋒”?他唯一能感受到的,就是墨汁的冰涼、毛筆的柔軟、紅紙的粗糙,以及那墨汁在紙上暈染開來的奇妙變化。這種感官上的直接體驗,遠比我們坐在教室里聽老師講大道理要來得深刻得多。數據顯示,兒童通過觸覺和視覺進行的學習,記憶留存率遠高于單純的聽覺學習,能達到70%以上,這可不是什么危言聳聽。我們非要等到孩子能夠用邏輯思維去理解這些藝術形式的時候,才肯讓他們接觸,是不是有點太遲了?文化,首先得是個能摸得著、看得見、玩得轉的東西,而不是供奉在神壇上的圣物。
家庭氛圍這東西,有時候比我們想象中要厲害得多。朗朗家那種浸潤在筆墨里的環境,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這讓我想起隔壁老王家的孫女,老王愛拉二胡,整天咿咿呀呀的,結果他三歲的孫女,雖然拉不出一個完整的調子,但那《茉莉花》的調子,哼哼起來有模有樣。這難道是報了什么音樂啟蒙班的結果嗎?顯然不是。這就是環境的力量,是一種無形的“文化因子”在起作用。這種家庭氛圍里的熏陶,其效果往往比我們刻意安排的“文化教育”要來得更自然、更持久。根據一些教育心理學的研究,家庭環境中的文化氛圍,對孩子價值觀和興趣愛好的形成,具有高達60%以上的影響權重。我們總在抱怨孩子對傳統文化不感興趣,有沒有想過,是我們自己先把這些東西跟“枯燥”、“困難”、“高深”這些詞聯系在了一起,然后不自覺地把這種負面情緒傳遞給了孩子?朗朗家的做法,至少證明了,傳統文化也可以是輕松愉快的,是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的。
更讓我覺得有意思的是朗朗媽媽的做法。她把朗朗寫字的過程拍下來,發到網上。這事兒,往小了說,是曬娃;往大了說,這就是一種文化傳承的“接力棒”。現在很多家長,一提到讓孩子學傳統文化,就滿腦子都是“這有用嗎?”“這能考試加分嗎?”這種功利性的焦慮,簡直要把文化傳承給綁架了。朗朗媽媽的做法,恰恰是在告訴這些焦慮的家長:有用沒用,先別急著下結論,讓孩子先在文化里撒個歡兒,玩個痛快再說。這些視頻、照片,記錄下的不僅僅是孩子的一個個瞬間,更是孩子與傳統文化之間建立聯系的證據。等朗朗長大了,某一天突然問你:“媽媽,我小時候為什么老喜歡寫毛筆字啊?”你就可以把這些視頻翻出來給他看,告訴他:“你看,你那時候就這么喜歡玩筆墨,這可是你自己選的愛好。”這時候,文化傳承的故事,才算是真正開始了。根據一項針對青少年文化認同感的研究顯示,那些在童年時期有具體文化體驗(如參與傳統手工藝、節日活動等)記錄的青少年,其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要顯著高于沒有相關記錄的青少年,比例大約高出35%。記錄,就是把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間,變成未來可以回味的寶藏。